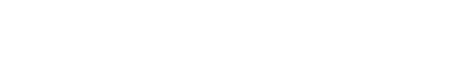让我来谈学术,觉得勉为其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热爱学术,但学术做得并不出色。但《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的邀请,以及年轻学子的热情,又动摇了我不做任何点评的决心。我想,王国维对做学问的总结,应该也是我的心声: 第一层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二层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第三层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我,要做到第一层次已是难得,做到二三层次,却绝非易事。 做学问不问柴米油盐,自然是很高的理想与境界。我想,但凡不是圣人,可不必效仿。涉及到学术的事情虽算不上神圣,但总结自己的经历,也有几点可以谈谈。首先,学术是需要理想的,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兴趣、专注、投入和定位; 其次,学术不等于论文、课题与名声; 第三,学术的终极主张是实现的人生理想。
一、学术
对于做学术而言,以下几点不可或缺:
( 一) 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研究学术来说,这一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兴趣的最大好处在于,你不是由于外在的诱惑、压力或者报酬而去从事你不喜欢的领域。很多人可能没有内在动机却做出较大的学术成就,但从大样本量上统计,有内在兴趣的人所做的学术成就显然高于没有学术兴趣的人。譬如,学生常常根 据家长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研究生涯; 根据就业市场的偏好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 根据冷门、热门来定位自 己的路径; 祈求老师指定课题来从事研究; 发表大量低端论文以迎合晋升需要等等。这些迫于外在压力或者报 酬所做的选择很难使一个人维持一生热情去追求学术生涯。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的最高理想 的影响,大部分人在取得一定研究成就之后转身从政,渴望声名而远离学术。
( 二) 专注
我们周围的世界有太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十年板凳冷”、“十年磨一剑”的现象不再常见。无论是电视、 报纸、网络、书籍,对超级明星人物的过度渲染,使学术的环境变得日益浮躁。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潮,使学术理想变得不值一钱。里钱外学的文化思潮和痞子文化,侵蚀学子和学者的根底。“行政猛于虎”使学术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重视应用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抛弃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复制、浅薄成为学术的通
行证。“快餐式”的培训和就业压力的短期效应无疑造就了低端人才和“钱学森之问”。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 研究者来说,就业不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理想便是学术的理想,学术的理想便是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理想。我们学术的理想遭受了太多儒家思想的包袱,真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的学问者最高理想无非 是“平天下”,即使智慧如圣人的孔子,也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感叹。在当代,如此复杂环境和人 类需求多样的诱惑之下,专注于学术是非常困难的。但要想实现学术的理想,必须“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 三) 投入
《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的作者斯密斯和希特总结了 32 学术大师的研究足迹时发现,伟大的学者具备 四种特点: ( 1) 热情; ( 2) 坚持不懈; ( 3) 纪律; ( 4) 创意。其实,这四个方面都与投入有关。对于抱有学术信仰的人来说,投入是实现学术理想的必要保证。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没有持恒的努力,即使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他也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研究者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持续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年轻时候的投入。
( 四) 定位
正如斯波尔丁所说,“你的信仰来自于你的信念,而不是仅仅是你的感知”。作为一个学者或者即将成为 学者的人,定位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借用武汉红金龙的企业愿景,“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对学术的 定位也是如此。张闻天先生曾经教导我们,“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我们有什么样的学术的理想,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理想的学术。当听闻英国政府将减少基础研究资金预算,增加应用性科学研究预算时,物理学家霍金坦言,如果方案最终通过,他将离开英国。打开大门,迎接实际,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学术真正的 目的,或者说定位,不是对直觉的阐释,也不是对理论的初步应用,不是曲迎外部的压力或者需要,而是探究事实的真相。
( 五) 创造
学术要建立自由的氛围,以利于学者的创造。在一本近四十万字的《创造性: 发现和发明的心理学》书中,以 91 位名人做例证、专门探讨创造力的专著,竟然没有一位中国人的影子,这确实让人担忧。学术的原动力不是复制、重复和浅薄。作为一个教师,必须身兼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责任。创造是一个 学者最有生命力的根基,也是作为学者的良知。学术的创造既可以是宏观上的理念、概念与体制,也可以是微观上的内容、过程或者方法。尽管近期许多学者提倡建立中国式模式( 例如,中国式管理、中国式领导) ,但很 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运用的是西方的方法、研究过程,甚至思路,中国模式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时代需要大理论,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和理念。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情景塑造了不同的 社会行动模式和价值观,也决定了不同的理论模式。
二、文章
( 一) 学术非文章 做学术离不开文章,但写文章不等于做学术。有人将西方学者划分成三种类型: ( 1) 文章型; ( 2) 讲课型;( 3) 思想型。尽管分类可能不完全概括出当前学者的形态,但也说明一些道理,学术不仅仅等同于文章。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在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传播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如果仅仅将发表论文作为一种衡量学术的标准或者学者价值的标准,则有误导的嫌疑。当今对知识工作者的考核,几乎都沿用对企业生产人员、销售人员的考核,以计分的方式,采用量化的指标,设定极短的时限( 譬如一年) 进行。这种考核方式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累积性的论文蜂拥而出,结果论文的质量,论文的贡献却不足够。另一方面,过分考核文章,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研究和发现本身转移到对文章发表的功能性目的上,造成对学术的伤害。 全国合法刊物 1 年可发表论文 200 万篇,与接近 1200 万人发表论文的需求相比,供需比为 1: 5。很显然,论文崇拜( 当然也包括课题崇拜) 在我国非常盛行。如果按照当前评价科研标准,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也评不上教授,文学家钱钟书别说评上教授,连上大学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一味崇拜论文( 课题) 不是一个学者应 有的学术理想。
作为一个学者( 未来学者) 来说,研究本身可能是很枯燥的。发表论文,特别是有思想的论文可能带给作者极大的喜悦,循环往复也促进学者的研究热情。追求论文数量或者追求论文的功利性目的,可能削弱研究本身的意义和我们的内在动力。因为一旦环境变得更好或更恶劣,研究的热情可能会消失。譬如,许多研究者职 称晋升后研究动力消失,研究热情下降,高质量的产出随之降低。
很多研究者以为,发表在一流期刊上的论文一定是有价值,高质量的论文,我对此是有异议的。高质量的期刊往往对论文的规范性、风格、甚至写作标准都有详细的、繁琐的规定。对新思想或者新构念、新模型持否定 态度。一篇思想性很强的论文,经过雕琢后,变成不是自己思想的东西。一流的期刊也往往是传统的期刊、主流的期刊,对“异类”或者“异端”加以排斥。例如经济学家贝克尔有关婚姻经济学的论文辗转 15 年才得以发 表。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也因太过出格,以至于过了两年( 1957 年) 才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表。
作为年轻的学者,严谨对待学术与论文的关系显然是必要的。好的学者不必过分追求论文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追求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在写作论文上过于急功近利,会对以后的科研生涯造成不利影响。例如,华裔学 者陈明哲先生发表在美国顶级期刊《管理评论》上的文章用了七年时间。虽然论文和学术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学术研究的价值却可以通过论文得以传播。因此,年轻的学者不应刻意追求功利性的论文发表而粗制滥造。积累对于学术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朱德所言,“多有积累,后必有成”。
( 二) 思想 学术研究或者论文写作的最大价值就是其思想。一篇思想性强的文章胜过 100 篇没有思想性的文章。思想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根基,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亟待纠正的问题:
1. 迎合实际。理论来源于实际,但理论高于实际。好的理论必定有好的思想性。“问题”主义过于强调解 决实际问题,而抛弃了理论的本原。很多研究建基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但,提出的问题是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分析的问题是别人已经分析的问题,解决的问题是别人已经解决的问题。思想性 很差,而以为迎合了实际,描述了现象就是理论。实际上,理论是实际的抽象,是在实际的基础上的提炼和凝结。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经常有学者提出反证,“现实生活中,有与你所说的不同的领导模式”。殊不知,研究者通常会 调研几百甚至几千个样本,而且样本中也会存在反例。个案是可以反映研究问题,但大样本量更能说明问题。迎合实际的结果可能是,直觉决定理论,而不是理论决定结果。譬如,我们可能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
2. 补篱笆与打桩。一些学者将学术研究者区分为三种类型: ( 1) 补篱笆型; ( 2) 修篱笆型; ( 3) 打桩型。补 篱笆型学者是对旧有理论的修修补补,力图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弥补,而没有任何的思想型,譬如拿美国的量表在中国测验,验证跨文化的特征。这种类型的研究者可能占有大部分。修篱笆型则是对原有理论进行 拓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拓展性的或者新的理论。这种研究者,要么改变原有的研究方法对原来的理论进行研究,要么运用旧有的方法,对理论进行拓展。这种类型的研究者也非常多,譬如自 Burns( 1978) 提出变革型领 导理论之后,很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拓展,最著名的有 Bass 和 Avolio 等等。而打桩型的研究者,则是建构自己的新 理论或者新方法。这样的研究者在现实之中只占少数,但也许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例如,明兹柏格对经理人角色的研究、赫兹柏格对双因素理论的研究、黄光国对面子和人情的研究、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研究等等。
3. 职位与声誉。追求职位与声誉对于研究者来说也许无可厚非。研究者在好的职位上可以获取更多的 资源,有利于自己学术成果的取得和推广。在当前学术资源还不足够的情况下( 特别对于年轻研究者来说更是 如此) ,足够的资源池可以带来足够的学术推力。但另一方面,获取职位资源,会耗费大量的精力、物力甚至财 力,这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和灾难性的。这不仅削弱研究者的内在动机,也可能使研究者走入学术的“道德陷阱”。
声誉的获得也可能有同样的道理。声誉一方面可能带来学术交流上的方便,申请课题的便利以及发表论文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研究者沉浸于过去的功劳之中,忙于应酬,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声誉很容易 让一个学者陶醉,让一个曾经勤奋的学者变成一个不思进取的、罩满光环的学者。在网络发达的年代,造神容易灭神难。
年轻的学者需要正确对待职位和声誉之于学术的关系。职位和声誉并不意味着学术的深度和思想,只是修补篱笆型学者的崇拜和狂热而已。张维迎认为,在高校,“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思想越严重。”一个真正 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也许不是情商很高的教授,他们通常很自信,也非常欣赏自己的学术创造。他们通常以 学术成就而不是官阶来衡量自己的地位。
4. 英语至上。在当今社会思潮中,英语至上主义是本土化研究式微的病根之一。著名学者杨叔子曾说, 我们的学生只知道 X、Y、Z,不知道长城在哪里。英语至上,不仅使本土文化缺失,也使研究取向唯西方马首是 瞻。现实中,学者们言必称英语,从学习工具、发表文章、研究取向、出国留学到引进人才( 例如各种学者奖励计 划) ,无一不是与此挂钩。大批西方的学术与研究被引进来,却难于消化,而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束之高阁。 大学以发表英文文章( SCI、SSCI) 为最高境界,例如很多大学对发表在外文顶级期刊上论文动辄奖励上百万元。 一些高校甚至规定,在 A 类( 外文) 期刊发表了论文就可以晋升职称。这种导向性,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本质。
近年来,海峡两岸学者纷纷对此进行质疑,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本土化研究模式,但英语至上的思潮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大批高质量本土论文投稿到英文期刊得不到发表,而国内期刊却缺乏广泛的、高质量的论文投 稿。要改变这种思潮,不仅仅是学者本身的责任,学术体制也必须检验自己的缺失。
学术的潮涌现象,使转型的中国学术研究遭受巨大冲击。这些研究为我们创造新理论划定了边界和提供 基础。在现有的情景下,我们是接受西方文化,运用经验数据来证实这些理论,还是二元对立或者建设性对话,建构我们本土化的理论或是具有普遍化的理论? 事实上,本土化的研究应该是现代的、发展的、有学科分类的 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完全的去“西化”,也不是一手拉着西方研究方法或者范式,一手操盘本土概念和变量,而是要扎根到中国社会实践中,去洗礼、炼狱、结晶,然后寻求用什么来表达它们,建立中国式管理。它是一种二元契合论,主张在中国的情境下,做出普遍的理论和范式,通过检验,达到知识的累积和增长。
5. 研究生培养。谈到学术与人生,自然离不开研究生的培养。现有的培养模式,更有可能使高校成为一 个职业培训机构,而不利于培养具有学术理想的莘莘学子。我们关心更多的是实际问题,譬如研究生就业,而较少的关心学术理想与理念。教师的授课不是以思想的创造为主题,而是以如何操作,如何就业为主题,这使得学生的学术价值变得极其低廉。大学不是一个盈利机构,也不是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尽管大学需要维持生 存,需要有杰出的校友,需要面对各种社会压力,但大学始终是一个创造思想的场地。大学不是为了在学校工作的人而存在,大学是思想的集聚地。研究生的培养如果仅仅着眼于就业,而不是思想碰撞,理论创造,大学的 理想就会消亡。
培养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传承大学理想不仅需要学者们持续努力,也需要反思学术理想和检阅学术体制。 年轻学子可能并不缺乏宏大的政治理想,最欠缺的也许是高尚的学术理想。
( 三) 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对于实现学术理想是非常关键的。文化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简称。文化构成整体词始于汉代经济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泰勒认为,文化包含知 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一切的其他才能和经验在内的综合体。文化是 一种规则,潜移默化的规则,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信仰。优秀的大学,它的文化应该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和创新。大学文化包含大学之精神与理想,因此大学文化的传承就是学术思想的传承。
优秀的学术氛围和文化往往造就优秀的学者群,这也就是贝尔实验室闻名全球的原因。年轻的学者不仅要置身于优秀的文化之中,更要为塑造优秀的大学文化尽心尽力。但很显然,当前大学文化是脆弱的:
1. 官学结合文化。占有一定资源的群体必定是有职位的群体,这使得大学成为政治的发源地。官学结合 的文化,使学术和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为可有可无之事。经常听一些领导者坦言,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领导者尚且如此,研究者何其悲哀? 官学结合使我们不仅不重视学术研究,更严重的是侵蚀了年轻 学者的学术志向。
2. 就业文化。大学本是盛产思想和学术的地方,却变成就业的代言人。学校不仅成立就业机构,宣传就 业的重要性,也强化就业管理和考核。这使大学从一个创造知识的场所变成一个“养鸡场”( 易中天语) 。学生 进入学校的理想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而不是传承学术理想。
3. 利己主义文化。钱理群认为,大学正在成为“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场所。就业、赚钱、当官,而不 是学术成为学生、学校和学术评价的标准。这些都远离学校的初衷。尽管精英学校离我们远去,学术的理念却 不可丢失。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学生胸怀天下,但起码我们教育要有这种气魄,要有这种理想。
论文和学术是思想的体现。作为学者,宋朝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太平”也许是我们学者的终极理想吧!
作者简介:韩 翼( 1970— ) ,男,湖北浠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